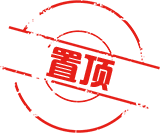
李碧华是位值得关注的作家。
李碧华写“痴男怨女,悲欢离合”,是一等一的高手,题材奇情怪异、天马行空。主题倾向于写背叛、轮回、凶杀、宿命;人物专注于写鬼、狐、妖;语言柔美、精炼、朦胧、诗意。总之,她善写奇人奇事奇情,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审美之路。在传统文学之外,用现代性的视角反思当代香港社会,增强时代的身份认同;严肃文学之外,又延续了传统文学传奇性的叙述,增强文本的可读性。
看了影片《霸王别姬》,读了原著《霸王别姬》;看了影片《胭脂扣》,读了原著《胭脂扣》;看了连续剧《生死桥》,读了原著《生死桥》……李碧华的才华才思才情,跃然纸上,有目共睹。
《霸王别姬》是华语影坛的最高峰,这不是溢美之词,实至名归,已经写过.这次,我们谈谈又一座次高峰—《胭脂扣》。
一、芳华绝代,寒凄彻骨的故事剧情。
《胭脂扣》,顾名思义,扣脂粉、扣年岁、扣佳偶、扣情热,但却扣不住人心。景泰蓝的胭脂扣只不过是十二少漫长岁月的一粒微尘,但对于如花,却凝聚了一生,是阴阳两地唯一的羁绊和挂念。
《胭脂扣》讲述了一对恋人跨越五十年的爱恨纠葛。在香港报馆任职的袁永定(万梓良饰),遇到了一位前来登寻人广告的女子如花(梅艳芳饰),但她却无钱付广告费。永定要她次日再来,不想她坚持不肯,并神出鬼没般尾随他一路。在闲聊中袁永定惊讶的发现,此女子原是三十年代就殉情的一位女鬼。
早在三十年代,她是香港石塘咀的头牌妓女。在那风月的世界里,她爱上了人称十二少的陈振邦(张国荣饰),感情俨然已经浓烈到嫁娶之时。但由于两者身份地位悬殊,婚事遭到陈家反对,陈家乃名门望族,不接受妓女作为陈家媳妇。陈振邦遂打破常规,脱离家庭与如花同居,两人以胭脂扣定情。二人同居后染食鸦片,陈振邦乃一纨绔子弟,并无养家糊口之本领,经济日渐拮据。于是如花与振邦终订阴世之约,计划吞食鸦片殉情。结果如花死去,而振邦被救活。五十年后,如花在阴间苦等振邦不得,遂上阳间来寻。
永定和他的女友楚娟(朱宝意饰),同情如花的遭遇,倾力帮助她找人。五十年,沧海桑田,物是人非,要想找寻意中人,简直大海捞针,而如花七日期限又即将届满。袁永定与女友无意中发现当年一张《骨子报》,发现振邦原来在一家电影制片厂内充当临时演员。十二少经岁月的折磨,生活的变故,早已穷困潦倒。如花探知,曾经风流英俊的十二少苟活于世,先是和家里安排的表妹结婚生子,而后败光家产等实情后,伤心之余,将胭脂扣交还,留给十二少一句:谢谢你,我不再等了。剧末,十二少望着如花离开的背影,蹒跚着追出来:“如花,原谅我……”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她的名字。
二、梅张演技惊世骇俗,云落天外
《胭脂扣》的成功,有张国荣和梅艳芳演技的加持,这绝对不能忽视。
没有谁比张国荣更适合演十二少。一低头一皱眉全是优雅,一抬头一提眼全是风情,俯仰之间,玉树临风,潇洒倜傥。片中的十二少,回眸一笑,迷离的眼神,活脱脱就是鲜生的情种。他用自己的风情万种,撩拨着如花,撩拨着观众的情绪,你说,如花能不动情吗?观众能不艳羡吗?
没有谁比梅艳芳更适合演如花。她有烟花女子的风韵,有凡夫俗子的通灵,有旗袍裹身后散发的妩媚。一切烟花巷柳的脂粉柳黛,在她这里都有板有眼。梅姑时而温情的的动作,时而温婉的语气,时而空洞的表情,把一个掉进爱情坑里的痴情女演绎的淋漓尽致。你说,爱情能不凄迷吗?等待能不让人动容吗?
三、隐喻和对比,铸就永恒魅力
《胭脂扣》的故事剧情,在唐代传奇小说中早已是轻车熟路。但在叙事手法上采用的倒叙、插叙、蒙太奇效应等多种手法的混用,大大增加了影片的观赏性。这又是异于很多平铺直叙的小说和影片的地方。同时,一个影片能让人印象深刻,似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很大程度不仅仅是故事情节塑造的,而是故事背后的隐喻意义和对比参照继而使人遐想和引人思考实现的。
先谈隐喻。
其一:算命先生解锁的“暗”字。片中如花抽中一个“暗”字签,算命先生说是吉兆,因为“暗”有两个日字,“阳火旺盛,在人间”。如花听后惊喜万分,意味着五十多年毫无音讯的十二少有打探到消息的希望。希望总比绝望好,至少还有可能。
可细细一想,这“暗”字,也隐喻着十二少悲苦的结局:苟活于世的负罪感,寻而不得的真情,跑龙套艰难度日的晚年凄景……十二少即便活着,也是暗无天日,五十多年来苟延残喘,却比不过一位青楼女子有骨气和情义。
其二:十二少赠送的对联。“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此幅对联是十二少爱如花,如漆似胶的时候,在怡红楼所赠。表面是赞赏如花长得惊艳脱俗,有倾城之貌。但细细一瞧,实则伤感和颓废至极。梦、月、花,均不是永恒之物。梦是虚脱,月有盈缺,花有凋谢。即便轰动一时,璀璨一时,终究是短暂的贪享。最后只能天各一方,阴阳相隔。
其三:“胭脂扣”。作为定情信物,贯穿其中,连掇起故事线条。实则是用“胭脂”来“扣”住整个一生。如花也好,十二少也罢,都是被无情的裹挟着,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当然,痴情总被无情恼,有胭脂的一方必然睹物思情,得承受更多事件的追问和罪责。
接着说对比。
其一:十二少前后的变化。如花的外貌永远定格在最美好的华年,岁月不曾偷走她的容颜,但活在阳间的十二少呢?惨不忍睹。
年少时的弄潮儿,春风得意,一日看尽长安花。曾经青楼妓馆里洋溢着才貌双全的陈家少主,现今却是写满沧桑、孤寂、粗陋的糟老头子。靠跑龙套为生,满脸皱褶。
其二:场地和色调的变化。出场的妓馆里姹紫嫣红,各种叫卖、调情、戏谑、讨好,不绝于缕,热闹非凡。各路打扮着花枝招展的姑娘争奇斗艳。时过境迁,五十三年后,现代文明的曙光打在每一个角落。场地染上时代的烙印,幼稚园、商场、酒楼拔地而起。禁娼令后,色彩亦变得单调和收敛。
三:感情的变化。如花和十二少,为爱,可以双双殉情。现代情侣永定和阿楚呢,决然不会。以前的人爱的干脆和感性,现代人着爱的理智和世俗。人活一世,无非就是徒个开心痛快,享受生活带来的乐趣,为了情爱失去生命,实在不值得。通过与现代人的对比,如花和十二少的爱,才愈发显得轰烈。但轰烈后,也会毛骨悚然。得不到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胭脂扣》让人唏嘘和着迷的地方,很多都是通过用隐喻和对比的细节实现的。李碧华写的高明,关锦鹏导演的也不奈。
四、时空变换下,对如花选择的认知
每个年龄段,对如花的选择都褒贬不一,但有一种认知,肯定是大众共识:20岁看如花,怦然心动,对风尘女子的果敢和痴情充满敬意。30岁看如花,后脊发凉,为如花的纯情和思想后怕。
青春年少时,觉得爱情是生活最重要的东西,是精神和食粮,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生命亦不重要。和爱的人相拥而去,何尝不是伟业!可如今,已过而立之年,发现爱情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殉情的事,自然变成嘲笑他人的谈资,天方夜谭。对待爱的人,放手成全又何尝不是圆满。爱的体现可以更宽广,只要你愿意跳出井底之蛙似的视角。
李碧华写到,这便是爱情:大概一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蚋、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并无想象中的美丽。
女人贪爱,男人贪生,一场生死爱恋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在不同时代下,女性的爱情悲剧和命运走向。或许对于如花而言,那句“我不再等了”,宣告她的爱情走向真正的死亡,何不是一种解脱和释然。而片中的独立女性楚楚呢,经历了一场感人的“人情鬼未了”,想必也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细水长流,涓涓细谷,也能长久,即便长情不了,也会果断放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