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以“一口五香 天下无双”为主题的金不换黄淮古窖始祖战略新品发布会在九华山盛大举行,在今年成都春糖完成首秀之后,金不换2000迎来正式上市,金不换酒业以“黄淮古窖始祖”之姿,向行业宣告高端口粮酒的价值新坐标。三窖五香,为华夏酒城新添一瓶“亳香型”金不换酒业深植于世界烈酒核心产区——安徽亳州,坐拥国内罕见的明代古窖群,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宣德元年(1426年),曹操后人开办的永昌酒号,经过600年的不断代传承,这片窖池不仅是黄淮流域酿酒文明的见证者,更被业内誉为“黄淮古窖始祖”。到了清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胡翠儒在永昌酒号的大院内扩建窖池,创办天吉长酒坊,并一直经营到民国,直到亳州解放,公私合营,成立亳州第一家酒厂——地方国营亳县酒厂(金不换酒业的前身)。从明代永昌酒号,到清代天吉长酒坊,再到建国后国营酒厂,三朝窖池的传承有序,让金不换酒业成为少数完整保留“三窖”体系的酒企,并依托明清古窖池与两大非遗酿造工艺,凝练出独有的“三窖五香”风味。“金不换酒业不仅是安徽白酒行业的标杆企业,更是徽酒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安徽省食品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邵栋梁在致辞中表示,“金不换酒,淬炼的是匠心,坚守的是品质,连续三年荣膺‘黄淮流域地域地理标志奖’殊荣,用实力诠释了品质至上的永恒追求。以新品战略为契机,金不换酒必将进一步擦亮‘徽酒名片’,为振兴徽酒贡献重要力量。” 金不换白酒集团总裁支涛在会上表示,当下,白酒行业正进入一个新周期,如果用一句话表达新周期下的新风口,那就是“有独特定位、以圈层经营为主、高质价比的区域小而美品牌”,于是诞生了今天发布的战略大单品。支涛强调,我们以“诚”字立身,用“诚实酒”来对打“广告酒”,用高端口粮酒来对接消费者新周期下的新需求,用金不换独有的明、清、建国三代窖池,打造出三窖五香的独特口感,为华夏酒城亳州新添一瓶“华夏亳香型”!目标3年5个亿,重新定义口粮酒标准据了解,金不换2000凝聚明、清、建国时期三窖精华:50%明代窖池原酒、30%清代窖池原酒、20%建国窖池原酒,基酒均经十年以上窖藏。时光淬炼下,辛辣褪去,酒体醇厚饱满,入口柔和细腻。其“三窖五香”特色更显独到——鼻闻浓香,沾嘴米香,入口麦香,细品芝麻香,回味酱香,五香层叠,空杯留香持久。但在价格上却定位百元价格带,彻底打破“年份酒必高价”的行业惯例,以“质价比之王”的姿态,重新定义口粮酒标准。在颜值上,金不换2000在企业经典元宝瓶的基础上,历经187次近乎吹毛求疵地比例调整,进行了36处细节优化,使瓶身比例更契合当下审美。耗时5年研发出了全新高分子材料,喷绘出无限接近真金的质感,结合全新的“鎏金渐染”工艺,使高贵典雅的金色从顶部弥漫,渐变至底部的晶莹剔透,让金不换2000如经黄金洗礼,熠熠生辉。金不换战略组组长、知名战略定位专家张康在演讲中表示,在带有商务属性的“办事酒”场景中,具有共识价值的名酒成为首选,但在50-300元的“高端口粮酒”市场中,尚未有强势的心智品牌,酒质更好的金不换酒在“亲朋小聚”“政商好友小聚”和“高品质自饮”,三大场景常年受老酒友和经销商的青睐,同时,金不换酒利润空间可观,团购生命强劲。“正确战略+有效落地=确定性增长。”知名战略可视化落地专家、缔壹品牌·战略可视化联合创始人/CEO胡磊表示,接下来金不换酒业将围绕金不换2000打响战略可视化,以全方位品宣支持,助力区域市场突破,以品鉴会+回厂游双擎驱动,助力经销商的生意增长。根据规划,金不换酒业力争在3年内将金不换2000打造成为年销5亿元的战略大单品,使金不换成为高端口粮酒的代表品牌。(来源:酒食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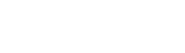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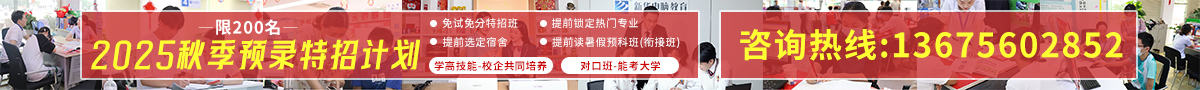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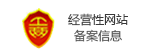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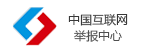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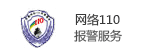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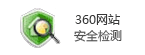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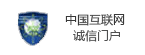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1582号
皖公网安备 34010402701582号